开先河与再书写:怎样把中国美术史写得好看
时间:2022-9-22 20:32:47 来源:文汇报
在图书市场繁荣的表象下,好书仍然是稀缺的,美术史、艺术史著作恐怕尤其如此。它们要么高高在上,长着一副拒绝普通读者的冷峻面孔;要么虽花团锦簇,可实际也就图个走马观花的热闹。反倒是近日重版的一本旧日经典和另一本新出佳作,给读者以新颖体验,并使人对中国美术史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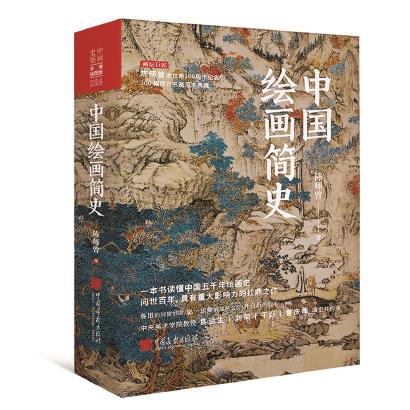
《中国绘画简史》陈师曾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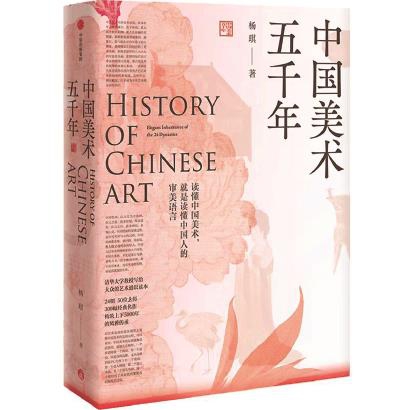
《中国美术五千年》杨琪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
读不懂的“中国美术”
前几日读到艺术史家杨琪的一篇访问,杨先生说在清华美院上艺术概论课的时候,每逢考试布置学生写作品心得,80%的人会选西方作品,只有20%选中国作品。后来杨先生参加评审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说课比赛,发现教师选择说课题材时同样遵循这一“八二定律”。何以如此,引起了杨先生的深思。他认为这和中西美术史的不同写法有关系:“你把西方美术史看完,把书合起来,想想这书讲了什么,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?能!那么中国美术史呢?唐宋元明清有那么多画家,你看完了,自问一下书里说了什么?不知道,那么多作品,记不住的。”
杨琪先生的观察我心有戚戚焉。出于爱好,我读过一些艺术史著作,观感和杨先生高度一致:西方艺术史不仅脉络清晰,而且著者能把脉络下的观念变迁梳理出来,便于读者记忆和理解;中国艺术史则总给人花团锦簇而云山雾罩之感——我知道它美、它好,却不明白美好在何处。当然,我并非在责怪编著者,不是他们不用心、不用力,而是按照西方艺术史的套路写中国艺术史确有难度。这背后的深层原因,恐怕是中西方思维的差异。
和西方古典哲学一样,西方古典绘画的目标是求“真”,力求客观准确反映现实和精神世界。而何为“真”、何以求“真”、如何判断求得了“真”,随着哲学(或神学)观念的变化而变化。这就有规律可循,有利于艺术史家进行抽象和总结,然后再传授给读者。中国画似乎不具备这个条件,因为它特殊。特殊在哪里?这个问题其实100年前就有人说清楚了。他叫陈师曾。
在初版于1922年的《中国绘画简史》一书中,作者陈师曾指出,中国画相当一部分由文人创作,是文人画。文人画讲究发挥“性灵与感想”,所求的不是惟妙惟肖的“真”,而是绘画者的真性情。文人画必须包含四大要素:人品、学问、才情、思想,缺一不可。具备这四要素,举凡山川、草木、禽兽、虫鱼及寻常所接触之物皆可“信手拈来,头头是道”。因此文人画中既有像王维、苏东坡、倪瓒这样飘逸悠远的神品,也有走奇崛夸张路线的“扬州八怪”。
文人画内部差异之大毋庸讳言,可无论哪个流派,都不以求真为目标。加上古人“书画不分家”,大画家往往兼善书法,而书法的“文人气”更浓。这就与以求真为核心追求的西方古典绘画明显拉开了距离,说两者属于不同“生物”或许也不为过。陈师曾就敏锐地指出,中国传统绘画“极不以形似立论”,西方古典绘画正相反,其“形似极矣”。
这样的比较略显粗疏,但的确点出了事情的实质。回到本文一开头提出的问题,正因为中国画文人气、不求真的特点,增加了艺术史撰写的难度。史家似乎很难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,结果就像杨琪批评的那样,史家讲了“那么多画家、那么多作品”,读者合上书依旧感到茫然。
当然,艺术史还是要继续写的,这是时代和社会的需求。大众需要好的艺术史。事实上,中国人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超过100年,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。陈师曾就堪称开先河者。
开先河的陈师曾
说起来陈师曾出身名门。1876年3月12日他生于湖南凤凰,祖父陈宝箴为湖南巡抚,是维新派骨干,父亲陈三立为晚清同光派代表诗人。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。陈寅恪曾自称一辈子钻研的是“不古不今之学”,意思是身处西方新事物潮水般涌入、深刻改变着老大帝国的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中的知识分子,所学所思必然是半中半西、亦新亦旧的。这话放在陈师曾身上同样适用。
陈师曾自幼饱读诗书、才华卓著,尤其擅长丹青。这是他传统的一面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在湖南推行新政的陈宝箴受到牵连被革职,全家迁居南京,23岁的陈师曾报考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。无论这是家庭安排还是个人选择,都凸显出他的另一个特征——趋新。
无独有偶,鲁迅也在1898年考入矿务铁路学堂,与陈师曾同窗。1902年,两人共赴日本留学,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。现有资料表明,鲁迅与陈师曾关系不错,周氏兄弟编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,封面就由陈师曾题写。归国后鲁迅和陈师曾同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,多有往还。1914年到1918年的鲁迅日记中提到陈师曾30多次,两人逛琉璃厂,互赠拓本,陈师曾还给鲁迅刻了枚印章,上书“俟堂”二字,建议好友蛰伏等待。鲁迅很珍视这枚印章,曾将所藏古砖拓本汇编为《俟堂专文杂集》,遗憾的是生前未能出版。
陈师曾还与蔡元培来往密切,1918年助其筹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。他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友谊也传为佳话。
从陈师曾的交游圈可知,他绝非遗老遗少一类人物。他绘画根底深厚,年少成名,却并未沉湎于其中,而是锐意创新。他师从海派画坛名宿吴昌硕,看重的就是海派的兼收并蓄;提携齐白石,则是认定他以虾米入画,别具一格。对西方绘画,陈师曾更是主张认真研究学习。他指出中国画对于光线远近的表现偏弱,应当用西洋画法补救,画家还要勇敢地“舍我之短,采人之长”,以自然为师,重视客观观察,采取科学方法,改进中国画。
这一观点,在《中国绘画简史》中做了进一步发挥。陈师曾紧扣住“交流”和“变化”这两个关键词,指出中国绘画从来不是闭关自守的,而是与外界广泛交流,从中汲取新知、求新求变。例如,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起,印度佛像艺术大规模传入中原,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古代人物画的发展,诞生了顾恺之、戴逵、张僧繇这样的大师。
正因为中国古代艺术是不惧来者、勇于创新的,这也给身处大变局中的陈师曾平添了几分底气。他慨然写道:“现在与外国美术接触之机会更多,当有采取融会之处,固在善于会通,以发挥固有之特长耳。”这与其弟陈寅恪推崇的“不今不古之学”有异曲同工之妙——唯有不今不古,方能杂糅中西,为中国画另辟新天地。这是陈师曾那代人的愿景。
100年后的相遇相知
从史学角度看,《中国绘画简史》也有其独特价值。我们知道,传统中国偏重记叙重大政治事件的“正史”,而缺少专门史。胡适1917年出版《中国哲学史大纲(上)》开创新风气,随后学界掀起撰写专门史的小高峰。尤其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,梁启超的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(1924)、许地山的《道教史》(1934)、蒋廷黻的《中国近代史》(1936)相继诞生。相比之下,陈师曾的《中国绘画简史》出版更早,可谓得风气之先。
今天捧读这本100年前的小书,深感陈师曾用简洁精到的笔触勾勒我国5000年美术史,功力非凡。他自谦本书只是“提示梗概,以为问道之津梁”,将来还要丰富完善。可惜天不假年,不久陈师曾染病去世,年仅47岁。
这之后,与中国艺术相关的通史类著作不断出现,其中也不乏名家名作。但不少著者陷入了罗列重要流派、代表人物和经典作品的套路,少有陈师曾这样清晰的脉络和清通的文笔。结果就是,杨琪批评的“书里说了什么?不知道”的糟糕体验占据读者心智,以至于大众望“中国美术史”而却步。
所幸近十几年情况显著变化。随着海外中国艺术史著作引进,人们的选择多了,艺术史也变得好读了。例如,迈克尔·苏立文注重中国艺术与其他文明艺术的互动与影响,高居翰从“艺术赞助人”的角度解析传统绘画活动,巫鸿结合考古学、人类学探索中国艺术的内在机理,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本土学者也奋起直追。杨琪于2022年5月推出了《中国美术五千年》——杨先生显然不满足于“开嘴炮”,而是亲自下场,揭示中国画发展的规律。本书图文并茂,按照时间线讲述中国美术的风格演变、技法沿革及题材变迁,解析历代作品中蕴含的中国人独特的精神追求,并告诉读者中国画究竟好在什么地方。
书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:“西方绘画的基本理论就是,绘画是对自然的模仿。他们争论不休的问题是,绘画究竟是自然的‘儿子、孙子还是老子’?而中国绘画表现心灵,对于西方画家争论不休的问题,给出了自己全新的回答——绘画不是自然地‘儿子’‘孙子’,绘画就是我自己。画如其人,画就是我,我就是画,画我同一!”
这不正是陈师曾揭示过的中西方艺术观念的相异之处吗?当然,杨琪表述得更加清晰:西方艺术的理论基础是“人对自然的征服”,中国艺术的理论基础则是“人与自然的和谐”。这同样是中国文人画的至高境界。我隐隐觉得这里面发生了一场“隔空对话”——陈师曾,这位中国美术史的首位书写者;杨琪,这位中国美术史的重写者,两人时隔100年后在我的阅读视野里相遇相知,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这是作为读者的幸福时刻。(唐骋华)
版权与免责声明:
【声明】本文转载自其它网络媒体,版权归原网站及作者所有;本站发表之图文,均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大众鉴赏目的,并不代表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。如果发现有涉嫌抄袭或不良信息内容,请您告知(电话:17712620144,QQ:476944718,邮件:476944718@qq.com),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删除。版权所有 2019-2020 上海麟驾艺术品信息有限公司
Copyright 2019-2020 Cnarts.net.cn Incorporated. All rights reserved

|
 |
 |
 |
 |
沪公网安备 31010102006431号 |



